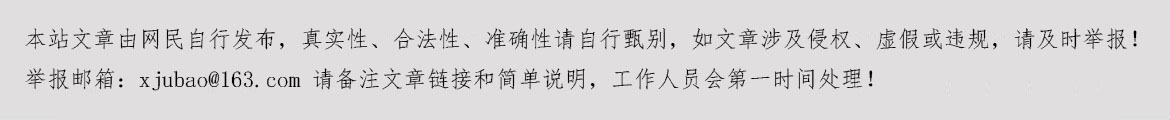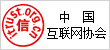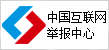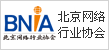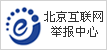领秀网是领先的新闻资讯平台,汇集美食文化、商旅生涯、国际资讯、投资理财、热点新闻、教育科研、等多方面权威信息
获得三枚一级勋章的罗厚福,为何仅为大校,老战友坦言:他太厚道
2021-06-08 15:38:02
染色体筛查 http://www.jiaenhospital.com/Zhuantimk/8.html
昨天,笔者发表了一篇文章《得知老首长仅为大校,开国中将流泪:这不公平》。看得出来,不少读者对罗厚福将军的事迹非常感兴趣。
遗憾的是,受限于篇幅和时间限制,笔者没有把罗厚福将军低授大校的原因写清楚,不少读者意见非常大。今天,笔者就谈谈这件事,算是填昨天挖的坑。
中将林维先看到昔日救他一命的教导员罗厚福仅为大校,不禁流泪:“论资格、论贡献,这不公平哇。”
林维先大校
的确,眼前的这位大校早在红军时代就是赫赫有名的游击师长,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新四军五师的旅长,在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江汉军分区司令员、鄂西北军区副司令员。
曾和他一起并肩战斗的战友,基本都在军以上单位担任领导职务。
罗厚福哈哈大笑:“算个么事哟,衔子又值几个钱?你当省军区司令员,我当省军区干部部部长,长江后浪推前浪,革命新人胜旧人,这真是大好事啊!”
转眼到了1975年5月19日清晨,救护车载着病危的罗厚福,急急地驶出省军区大院。
省军区机关的同志们不约而同地来到路口,无言地目送救护车远去。人们心里在默念:老首长,你可要活着回来啊……
从昏迷中醒来后,罗厚福发现自己躺在病房里除了老伴外,再没有别人,病房里安静极了。
他的目光落在老伴红肿的眼睛上,他无力地摇摇头,微微地笑了。
老伴看着他。那曾是明亮锐利的目光,什么时候变得这般混浊和迟钝?她太熟悉这双眼睛了。
在大别山,在鄂西北,在血与火的战场上,在无论什么艰难困苦面前,那目光从来都是坚定的、充满信心的。
只有一次是黯然忧郁的,那一次只有她知道。
那是1951年的一天,罗厚福回到家里,他的目光第一次变得那样黯然神伤。
她问起,他实说了。
1948年初,刚解放的陂孝礼地区很穷,罗厚福不忍心看到和他打了多年游击的部下仍在忍饥挨饿,于是号召干部们拿出自己的钱做垫资,军分区也出一部分钱,办了一个卷烟加工厂。
工厂盈利后,不仅每个干部都得了利息补贴家用,而且也安置了不少烈属工作。但是,只过了两三年,大环境变了,这事成了靶子。
战争时期,一位保长曾舍生忘死地掩护过我们的许多同志,为革命作出了贡献,解放后由于种种原因,日子过得相当艰难。
保长找到军分区,罗厚福拍胸脯:人家对革命作过有益的事情,我们不能忘记。
在他的提议下,组织上安排那个保长在烟厂当了工人。结果没多久发生镇反运动,出事了。
罗厚福大会小会检讨了十多次,最后从副军职降为准师职。
原本五五年要授予上校军衔,新四军五师的老师长写了封信给省军区:“罗厚福是个老同志,怎么能授上校呢?”遂改大校。
对于这结果,罗厚福一开始是想不通的。但很快,他的目光又恢复了坚定,他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弄清楚。
但是,整整24年过去了,朝气蓬勃的罗厚福已经两鬓染霜、风烛残年了,可问题仍然没有搞清楚。
不少了解事件内情的老部下已经在大军区当官儿,为他鸣不平:“我们写了封信帮你作证,你拿去北京找找李、王两位老首长。”
罗厚福一笑了之:“这么一点事,不划算!”
老伴抱怨说:你的下级都当上大军区一级的干部了,可你……”
罗厚福火了:“亏你还是个老同志,竟讲出这种话!”
罗厚福始终没有找任何领导,也没有再向其他人提起那段不愉快的日子,包括来看他的开国中将林维先。
现在,罗厚福躺在病床上,他很清楚,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想要留下什么话已经是时候了。但是,从哪说起,说些什么呢?
省委赵辛初书记坐在罗厚福的面前,长久地望着这位老战友。
当年,赵书记还是孝感县委书记,罗厚福的六大队则活跃于孝感、黄陂一带。三十五年来,他们共同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一次又一次的生死的考验。
罗厚福打破了沉默:“你工作忙,不该来的?”声音很微弱,但很清晰。书记的语调是平静的,“省委的同志都问你好!"
罗厚福的眼圈红起来,一汪老泪在眼眶里打转。
赵书记竭力抑制住自己的感情。他理解这位老战士的心。想到那段至今还没有纠正的历史,书记感到对不起这位被称为“坚持大别山斗争的一面旗帜”的英雄。
罗厚福解嘲地笑笑,把话题转到其他方面:“上半年全省生产任务能完成吧?”
省委书记的喉咙哽塞了,但他还是讲了下去。
一谈就是三个小时。
医生们尽了最大的力量来挽救这个倔强的生命。但是,一切都已经晚了。
一阵紧似一阵的心绞痛,把他推向了死亡的边缘,生命垂危,奄奄一息。
忽然,罗厚福睁大眼睛,久久地看着守护在床前的老伴和同志们,他嘴唇蠕动着,似乎有许多话要说。
老伴伏下身子,耳朵贴在他的唇边。
“希望组织上把……51年的问题……搞……清……!”这是罗厚福最后的心愿。
医生宣布抢救无效,家属们失声痛哭,赵书记也潸然泪下,对罗厚福老伴说:“这个罗司令呀,哎,完全就是太厚道了!”
湖北省委书记赵辛初
的确,打了19年仗,有17年任务是留守残破的老根据地,不是厚道人,哪里会四次接受这样的任务呢?
罗厚福的厚道,早在战争年代就很出名。
一九四八年元旦。豫鄂三分区部队猛攻孝感。守敌凭借着有利的地形和坚固的工事,集中所有的轻重武器,向正面进攻的我军七连猛烈阻击。
七连指导员孙九平爬在一个坟包后面,指挥机枪手猛打,企图把敌人火力吸引过来,组织部队强攻。但是,狡猾的敌人根本不理睬,七连几次突击都没成功。
孙九平暴怒地叫喊着,两个机枪手都没有反应。他伸手摸去才发现:机枪手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牺牲了。气急地甩掉手中的大片刀,挽起衣袖,抱起机枪,发疯似地扫射。
火舌从坟包后猛烈地喷出,敌人两挺机关枪成了哑巴,火力明显地减弱了。
冲锋号骤起,战士们跃出坟包,猛扑向敌人阵地。敌人招架不住,弃阵逃跑,战士们不顾一切地奋力追杀。
孙九平右手握着大片刀站起身,左手狠狠地抹了把汗,向通信员大声命令道:“快报告罗司令,北门已经打开,正……”
话没说完,孙九平突然栽倒在地上。通信员连忙俯身托起。借着黎明的曙光,只见孙九平头部中弹,满脸血污,不省人事。他惊慌地大嚷:“卫生员,快,快来!”
不知什么时候,孙九平醒过来了,可眼前一片漆黑。
来看他的罗厚福心里难过极了,他了解这个坚强的指导员。留守鄂西北时,孙九平给他当警卫员,他们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结下了生死与共的深厚感情。一口干菜匀着吃,一床被单伙着盖。
这位机灵的警卫员曾多次央求罗厚福:“等胜利了进到汉口,先一起去瞧瞧黄鹤楼。”
可是,谁也不曾料到,黎明前的最后一仗,他却失明了。
临走前,罗厚福拿出几块大洋,交给村长:“想办法,一定帮他尽快成个家,他不是瞎子,是英雄!”
村长连连点头:“这事儿包在我身上,罗司令您放心!”
腊月二十三,孙九平在村里举行了婚礼,新娘子是一个贤惠、温柔、善良的农村妇女。
罗厚福从数十里外专程赶来祝贺。他为新婚夫妇送来两床新被子,一条床单和两块光洋。
1953年,罗厚福调到湖北省军区工作。一办完报到手续,他就专程请假回到孝感,把孙九平接到了武汉,带着他走遍全市医院,请最好的医生治疗,但最后一线希望还是破灭了。
罗厚福不忍心把这消息告诉孙九平,而是带着他游遍了武汉三镇的风景名胜。
向着黄鹤楼最高处拾级而上,罗厚福强忍悲痛:“朝前看能看见武汉三镇,再远处就是山,蓝幽幽的,像蒙上了绸子哩。”
罗厚福的老战友甘景元,红军时期曾任师政委,率领战士们东征西讨,浴血奋战,打了许多胜仗。
抗日战争爆发后,甘景元先后在豫鄂挺进队和新四军第五师搞后勤,他勤于运筹,精心计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保证了几万大军的衣食住行,被称为好后勤。
1940年秋,十四旅主力白马山和日军一个大队接上了火。那一仗打得真残酷,枪炮声两天两夜没停,给养跟不上,战士们饿着肚子和日本鬼子死拼。许多同志连举枪的气力都没有了。
旅长罗厚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弄不到吃的,这场伏击战将会前功尽弃。
正在紧急关头,甘景元和两百个战士挑着担子,冲过硝烟弥漫的战火赶到了阵地。
罗厚福抓住甘景元的肩膀,劈头盖脸地质问:“你这后勤部长么样当的,我的人都快饿死了!”
甘景元笑笑,不慌不忙指指刚放下的担子。罗厚福过去一看,竟是两百多担馒头。
真是雪里送炭哪!罗厚福大笑起来,抓起一个就往嘴里塞,边嚼边嚷:“伙计,这场战斗,你应立头功!”
日本投降后,国军调集三十万人马围攻中原军区,中原军区所属各部分路突围。在那次突围中,甘景元脚被打伤了,掉了队。
他连走带爬,在荒山老林里挣扎了整整三个多月,最后才在老乡的掩护下,避开了敌人的搜查。
也就从那时起,甘景元与党和部队失去了联系。伤好后,落下了残疾,他跛着脚回到了家乡。
回到家后,甘景元日子也不好过,由于老红军+老新四军的身份,他的家被还乡团洗劫一空。
为了躲避追杀,甘景元带着家人躲进深山,住在一间破旧的茅草房里。没吃的,没烧的,缺盖的,缺穿的,一家人在死亡线上挣扎。
1948年,除夕夜,罗厚福和地委书记一行奔波了一整天,傍晚时来到了甘景元那座低矮的茅草房。
甘景元一家六口又惊又喜,热情地招呼着除夕的客人。
屋里太小,甘景元把孩子哄出去。地委书记从怀里掏出一张公文,清清嗓子,宣布:地委决定,对甘景元给予老红军待遇,按月发给生活费和米、面、油、肉等生活物资。
罗厚福指着地上的米、面、衣物说:“老甘,我们来晚了!东西太少,先过个年吧!过完年回村里住,房子我们帮你建好了。”
罗厚福还没有说完,甘景元多病的妻子就挣扎起来,扑在两口袋米面上,嚎啕大哭。
甘景元走过去劝妻子,话没出口,自己的泪水也流了下来,止也止不住。
1949年10月,整个孝感县城沉浸在一派节日的气氛中。罗厚福的岳父、岳母把儿子送了回来,打算住几天就走,可是经不住儿女的苦苦挽留,一住就是两个月。
年关将近,两位老人思念故土,决定告别女儿女婿,返回家乡。
老人次日就要动身,这时,分区政治部民运科长悄悄走进来,将一张五百斤的米票放在桌子上,对罗厚福说:“这是组织上决定给老人作盘缠用的。”
当时实行的是供给制,米票是发放领取实物的依据。由于刚刚解放,群众生活艰苦,部队和机关供应也相当紧张,团以上干部每人每月才发给三十斤米票,所以组织上一下子拿出五百斤米票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罗厚福忙抓起桌子上的米票,拦住民运科长说:“不行,不行,我们过得去,这些米票留给困难的同志吧!”
民运科长推托着说:“司令员,这是组织决定,我个人也做不了主啊!”说着,挣脱罗厚福的手,逃跑般地离去。
怎么办呢?罗厚福和爱人商量来商量去,这五百斤米票说什么也不能要,但硬退给组织也不妥,想个什么办法呢?
突然,他想起了当旅长时的老部下——新四军五师十四旅四十一团团长聂太清。
1942年。在粉碎日伪扫荡中,聂太清在蕲春县境内同敌人作战三天三夜,保证了旅部和直属部队的胜利转移,最后撤退时负了重伤。
罗厚福急匆匆地赶来,见到自己的战友时,聂太清已是奄奄一息了。听到罗厚福的声音,他奋力睁开眼睛,苍白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宽慰的笑容。
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伙计,我先走一步,要是你能看到胜利,就把我送回老家……”
第二天,罗厚福用了一上午的时间,给聂太清的家属写了一封信,然后把五百斤米票、十块钢洋连同信一起给了通信员,要他赶快送去。
即使到建国后,罗厚福厚道的本性也没有改变。
特殊年代的一天夜里,张体学穿行在武汉水陆街的小巷深处。现在,深更半夜,家家闭门,到什么地方去呢?他抬头望望满天的星斗,侧耳听听远处的火车隆隆声:有办法了!
绕了一个圈子,张体学摸到省军区一位领导同志的家里。两人在深夜中相见。这位领导对张体学当时的处境十分同情,但考虑到可能发生的后果,没有留他。
张体学知道对方的处境和心思,也没多说什么,就准备走开。那位领导说:“你到罗厚福同志家里去吧!他那里偏僻,而且他又是免职治病,麻烦会少些的。”
张体学何尝没有想到罗厚福呢?抗战初期,张体学和罗厚福在新四军七里坪留守处共同带着一支由红军干部组成的小部队。
1941年,罗厚福任新四军五师十四旅旅长,张体学任政委。他们在战斗中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他怎能忘记呢?
张体学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罗厚福。但是,罗厚福身患严重的冠心病。在这非常时期,他不忍心去打搅一个疾病缠身的战友。
可是,现在不得不去找罗厚福了。
叮零,叮零,叮零,叮零。紧促的铃声响了四下。罗厚福知道是自己的同志来了。他翻身下床,穿上棉军装,急匆匆穿过庭院,前去开门。
开门一看,不禁吃了一惊。从张体学的形态和举止上,罗厚福心里明白了一半。他二话没说,把张体学拉进了屋里。
罗厚福关上门窗,沏上杯热茶,放到张体学的面前。
张体学抬起头,无言地看着老战友。罗厚福转过身来,两道目光相遇,用不着半句话,什么都明白了。
罗厚福打破了沉默:“就在这里住下吧,天大的事我担着!”
虽然彼此之间心是相通的,但张体学还是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他从沙发上站起来,把老战友的手紧紧地握了又握。